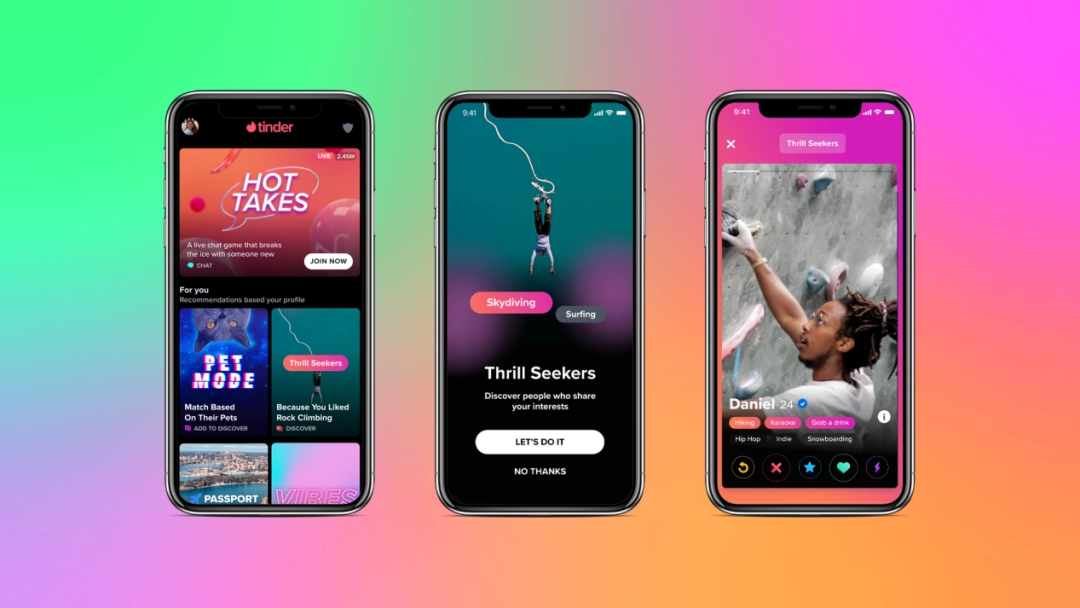整个毕者友对话很尴尬,从一个节目的角度批评许知远的表现,怎么都不为过。毕竟他并非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。但从一个男人的意淫角度去批判许知远,我觉得又未免太苛刻。从俞飞鸿的反馈来看,她并不是一个表达欲特别旺盛的公众人物,又或许是因为和许并不相熟。毕竟,在窦文涛的《圆桌派》上,俞飞鸿的表达更有安全感,更自如。
我得承认,采访是破碎的,是失序的,是完成度不够的作品——这更像许知远嫌兆更个人的聊天记录。我在看手槐(听)的过程,始终提着一颗心,生怕下一秒钟,从许知远的嘴里突然酣畅淋漓的吐露他这中年男人的爱慕之声。也许是疯狂,也许是露骨,也许是仓皇失措,也许是可怜兮兮——然后俞飞鸿嫣然一笑,满含教养的答谢,自如地反问,见怪不怪地凝视,温柔又直接的断然拒绝。
更重要的是,俞飞鸿是非常美好的女神,但她并不是“知识分子”,她的审美和思考是个人的,是流俗的,是倦懒的,是未曾刻意总结的。也许是不愿意,也许是不屑于,从采访本身透露出的,是俞飞鸿对于自己,并没有一种断然定论的归纳。于她而言,更舒适的表达,是对既往过去具体人事的陈述。换言之,她或许更倾向于用镜头化的语言,去陈述已经发生的一切。而不会以旁白式的语言,去为镜头前出现的一切,下脚注、做推论、谈畅想。
俞散发着满满的圆满自处,也就是深深折服许知远的秩序感。偏偏,许不断地用躁动的改变来撩拨俞飞鸿。真是千钧重棒敲在棉花山。事业的突破、审美的探索、情感的追求、认知的改变,许知远像青春期的男孩,在心爱的女孩面前,掏出了自以为的浑身解数,只换来她的浅笑。连这笑都是她固有的家教和礼貌,真诚得令人绝望。
所以,整个采访许知远一直在抛话头,也不断在丢话头。始终没有掌握聊天的主动权。聊天就是这么奇怪,有时候明明是你一直在说,在问,但是当你无法挠到对方的表达欲,你就只能始终徘徊在对话的门口,如果你还期待和任务,相信我,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聊天更令人尴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