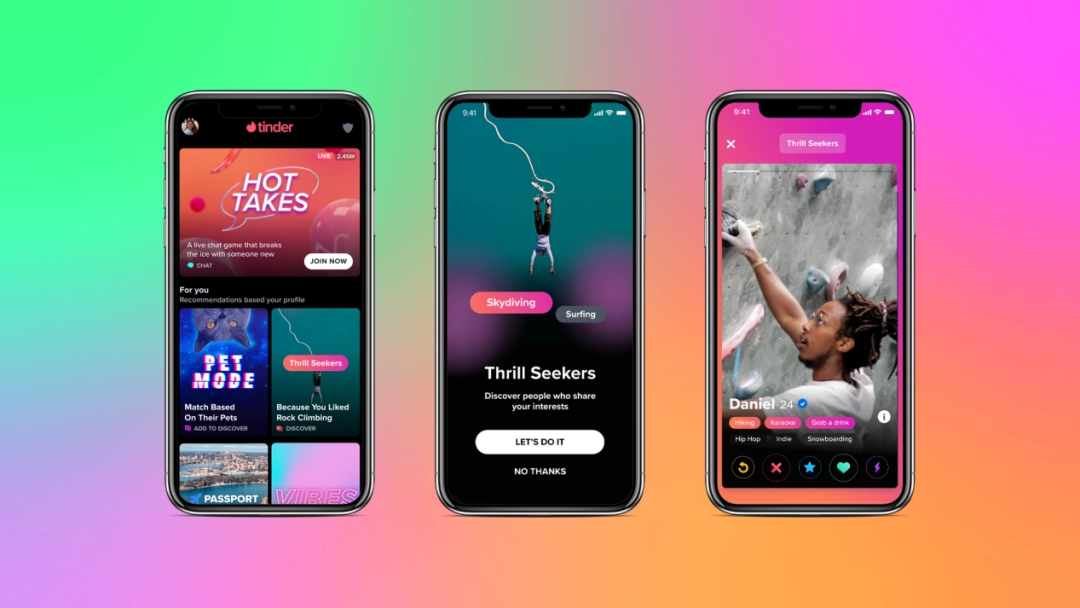数字是抽象的,诗歌是要用形象思维的,然而这两者结合,同样有佳作产生:可以是豪放的,“黄河入天走东海,万里写入胸怀间”;可以是细腻的,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;可以是沉痛,“三万里河东入海,五千仞岳上摩天。遗民泪尽胡尘里,南望王师又一年”;可以是感伤的,“六朝如梦鸟空啼”;可以是愤怒,“一朝封奏九重天,夕贬潮阳路八千”;可以是夸张,“孤臣霜发三千丈”;可以是讽刺,“三千宠爱在一身”;也可以是欢快的,“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”…… 不过,这些诗中的数字,仅是作“镶嵌”之用,真正的数字诗,必须是以数字为主体,如南朝民歌中的“江陵去扬州,三千三百里。已行一千三,剩有二千在。”可以解读为是一个长途行者的倦歌——他在不停地算里程;也可理解是一个远离家并滚乡,归心似箭的卜蔽正男子的情歌,期盼着早一点与心上人见面。——其实,路还长着呢。心理描写非常准确。 另一首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;门前六七树,八九十枝花”。个位基数词全无遗漏,又描绘了一幅恬淡宁静的田园风光,用之作为蒙童读物,型悔真是一举两得。 电视台曾播放过的《宰相刘罗锅》,内中有一处情节:乾隆皇帝手持一枝鲜艳的红花,将花瓣一片片地剥落抛撒,口中念念有词,“一片一片又一片,二片三片四五片,六片七片八九片”,刘墉信口接了一句,“飞入草丛都不见”。众人大笑。这出戏编得并不好,红花入草丛怎会都不见?明显有疏漏之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