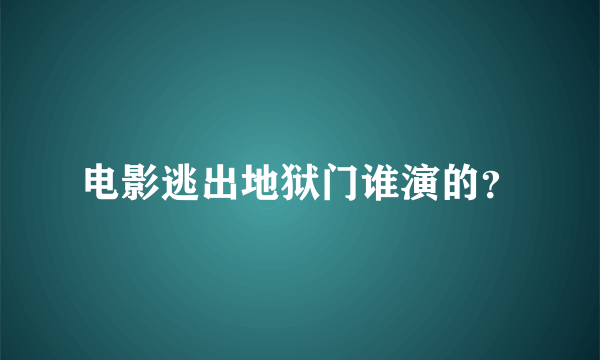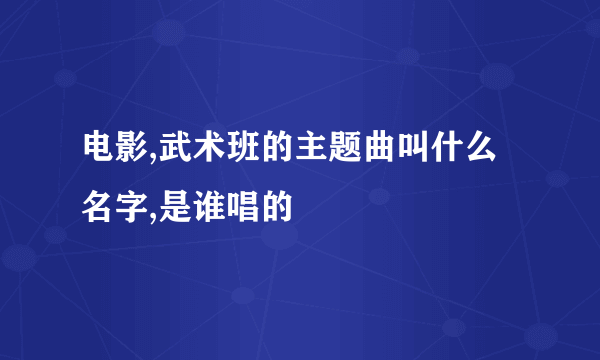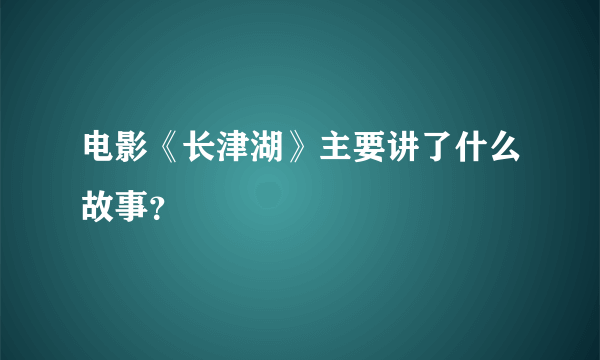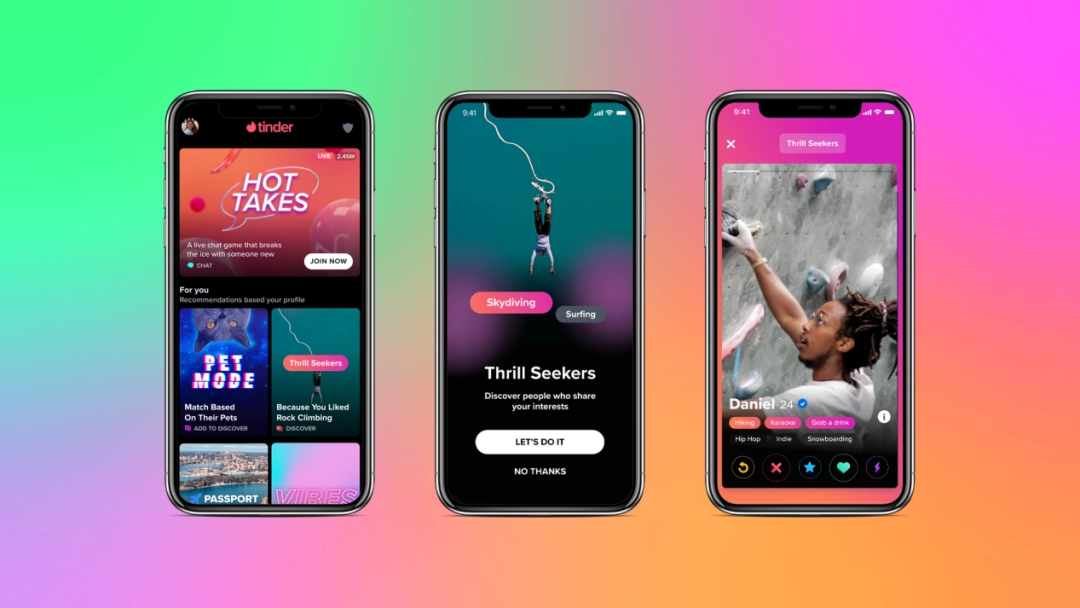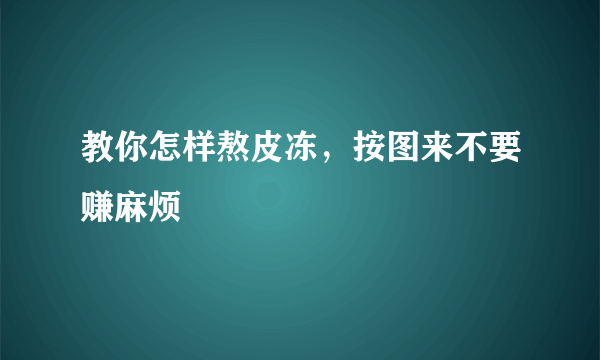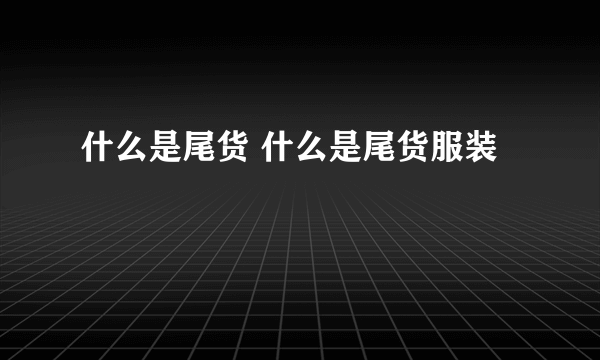我为什么要拍《两只老虎》?
一直要写一篇手记,但不知从何入手。有时候,做事情简单,总结反倒是难。
2016年11月,动了念头开始写剧本;2019年11月,《两只老虎》正式上映。整整三年。
上映的日子很巧,定在11月29日,感恩节过后的一天。想来也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,让我能够借此,向为这部电影付出过的每个人,向每一位《两只老虎》的观众,说一句感谢。
感谢你们,让这个孤单稚嫩的念头,得以走过这样长的路,长大成一个勇敢又丰富的生命,在大银幕上,一遍遍上演……
电影正式上映前,我到过很多城市,与各地提前观影的观众见面。每一次放映,我在后台紧张地大气也不敢出,直到听到黑暗中传来第一阵大笑,接着,是第二阵、第三阵……于是我才有勇气走上台,怀着最深的敬畏,去跟观众见面。
然后,我看见了一种复杂的情绪,是裹挟着生活重量的怅然;也听到一些哽咽的声音,是电影触发的他者共感。
过往际遇“成就”的情感,浓稠情感创造的作品,得以被这样感知。在这一刻,我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因而每一次站在台上的时刻,都不自知地变成了对过往的回望……
2001年中秋,我回家过节,我爸炒了菜。倒了酒,我头一天和狐朋狗友喝多了,我说我不喝酒,他挺不高兴的。第二天,我就离开了家。第三天,接到电话,父亲去世了。
再赶回去,三天前还忙碌着炒菜做饭的父亲躺在医院太平间冰冷的水泥台子上。我摸了摸他的脸,没有温度,和水泥台子一样冰冷和僵硬。
突如其来的死亡,我始终找不到合理的解释。好好的一个人,就这样没了,离开了,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某时某地再见,按已有的经验,应该是不会了。
后来,我看到姜文导演的一篇访谈,他说《鬼子来了》根本上讲述的是他对死亡的认知和恐惧;在宁浩导演的《长大成人》里,他说在35岁左右,他开始思考跟死亡有关的事情;在王朔老师的一本书里,他说“在人生最得意的一年里,突然父亲和哥哥,以及最好的朋友们梁左相继去世,像三个大耳光子扇来”,扇得他开始重新观察和思考人生。
当时的我,根本不知道,多年以后会和上述的三位认识,甚至成为朋友,一起工作。
当时的我,也根本没有意识到,在三十多岁时,自己会陷入相似的精神危机。
所谓的危机,是内心一直试图掩盖的恐惧,对死亡的恐惧,对失去的恐惧。恐惧掩盖了所有其他的情绪,谋杀了快乐。
逃避恐惧全然无用,但如要直面却也困难。
2014年,我得到机会,导演了自己的处女作《命运速递》。来不及伤春悲秋,便抖擞精神,一边与不时泛起的惊恐与抑郁战斗,一边拼尽力气把它拍完。还没拍完,我就知道超支了。做完后期,我已经比当导演之前还穷。电影无人喝彩,我快要没地儿住了。
后来,参加了FIRST影展,拿了奖,解决了温饱,又开始筹备第二部电影。几经辗转,没有弄成。
生活左手给你一块糖,右手跟着来一记老拳。
那几年,我的爷爷、三位舅舅、一位姑姑和姑丈相继去世。我和弟弟说,现在回老家好像就一件事——参加葬礼。
2016年,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机会,得以加入姜文导演的《邪不压正》的剧组担任编剧。我关掉了朋友圈 ,几乎和外界割断联系,用尽全部力气去工作。
在《邪不压正》中,彭于晏扮演的李天然一直在纠结中,少年时期,师父师母(也是养父养母)和世界就在面前被仇人惨杀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,我们称之为“应激性创伤障碍”。在国仇家恨面前,他迈不过去的,是自己心里的那道坎。
而姜文导演,即使智慧如他,在剧组的每一天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烦恼,承担着换我可能无法承担的压力与焦虑。
走到这里,我所得的际遇早已超越了当年的梦想。我突然明白了,梦想,其实只是贪欲另外一个美好的名字。梦想没有止境,实为欲壑难填。
被欲望绑架的人,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恐惧,为恐惧无法克服而忧郁,为想得到快乐而去盲目追求毫无必要的欲望。人生就这样陷入一种死循环中。
说到底,是把自己看的太重,自命不凡到所得统统视为应该,为不可得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们被钱绑架,被名利绑架,被过分要求的爱绑架。说到底,被自己绑架。
于是,这个时候,《两只老虎》的故事突然跳了出来。
张成功拥有了大部分人终其一生无法拥有的财富、地位和名声,但他想跳楼;余凯旋为了一份不必求证的证明铤而走险;周元、彩霞、范志刚、史剑,他们都陷入自己生活的泥沼中……
就像现实里的大多数,都在各自生活的困境里兵荒马乱,永恒的奔跑依旧要面对着空泛的明天。
新闻讲述着不堪重负而走上绝路故事的各种版本,生活里我被迫与好几位朋友“告别”。
有这个必要吗?这个问题,像多年前父亲的离开一样,得不到答案。
生和死、爱和恨、成功和失败、快乐和忧愁,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心里的两只老虎,一只笑着,一只哭着,它们象征着生活的两个切面,总在打架,没有输赢。如同《两只老虎》一样,生活的本质到底是一首欢乐的童谣,还是一个惨烈的故事,没有绝对的答案。
那些困顿的、失意的、无解的际遇,垒成了今天的我,也垒成了今天的《两只老虎》。既然忧伤与快乐不可能融合或消除,那就让它们打吧。
悲剧也是快乐,将来也是存在。
2013年,身体和精神都生了病的我,反反复复,不得见好。惊恐变成日常,救护车和速效救心丸就成了生活里的主题。直到有天,我和弟弟走在故乡的大街上,他说,我觉得,你还是没有从爸爸去世的这件事走出来……
回头想来,我之所以是我,也许就是因为那几件事情;对于我是,对于张成功也是。
尽管今天的我如此凝视过去,但过去的我却不会对今天的我瞟上一眼了。
所以我用《两只老虎》为之前的人生做结,是给自己的礼物,也是给每一个同样经历过欢愉与失意、成功与困顿的生活着的人们。
所有笑意爬行过后的沟壑,有了眼泪便又是运河。
假如有一个人,看完电影,走出影院,觉得此时此刻挺好。过往的苦闷与欢愉都不再捞取,往前走,往向往之地走,往无妄之地走……
那我就十分满足了。
假如余凯旋就是张成功的另一个人格。
《两只老虎》拥有葛大爷、赵薇、乔杉、范伟、闫妮、大潘等顶配阵容。
赵薇再度回归大银幕,葛优和赵薇的首次合作,更多期待还是这个几乎覆盖春晚小品半壁江山的阵容,能给我们带来暖心一笑或开怀大笑,驱散积攒到年底的寒冷。
结果,看完电影,笑不出来,却多了很多问号。
心里暗暗跟着《两只老虎》唱起来:真奇怪!真奇怪!
第一,《两只老虎》原来不是喜剧。
第二,作为剧情片,《两只老虎》依然很奇怪,尤其电影的结尾,葛优饰演的张成功莫名消失又莫名出现,更是一种非常后现代风格的处理。
感到奇怪,是我们套用惯常经验去解释一个我们不常遇到的情况。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问:为什么?
关于《两只老虎》,有一种解释可能是解开电影奇怪盒子的钥匙:即张成功和余凯旋其实是同一个人,余凯旋是张成功在自杀前,幻想出来的年轻的自己。
张成功不是真的被余凯旋绑架,而是临死前被年轻的人格拷问。
这一观点仅仅是解读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个观点,本文不想再找细节证明这一观点。
比如,两人一个叫“成功”,一个叫“凯旋”;一个属虎,一个也属虎,差两轮;一个开路虎,一个开标致小狮子;一个的父亲是诗人,一个理想也是当诗人……这些都可以当作证据。
假设就是这样的,余凯旋和张成功不是一个绑匪一个被绑,而是同一个人,试着用这个钥匙去解读这部电影。
首先,这部电影最难理解的就是片名,“两只老虎”到底指的是谁?
如果用“人格说”来解释,“两只老虎”指的就是张成功和余凯旋,一个本人,一个幻想出来的人格。
其次,《两只老虎》的剧情是靠张成功让余凯旋帮忙办三件事推动的。
但除了张成功郑重其事地要求余凯旋办的三件事,开始还有买牛排、红酒、雪茄和中间没有算数的打史剑,其实一共是5件事。
这5件事,对于“成功人士”张成功来说,是由当下到过去,从最迫切的口腹之欲到压在心底最深处的痛,由近及远,由肤浅到痛彻心扉的层层递进。
在自杀之前,张成功一层一层把它们宣泄出来,并借助了人格余凯旋。
张成功这5件事,时间上是由现在到过去回溯的,但如果从过去向现在捋,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张成功的一生。
而且,拥有这样波澜起伏成功人生的“张成功”,在我们周围比比皆是。
先说最后一件事,因为最后一件事是张成功人生的开始,而且是很悲惨的开始。
电影结尾,张成功让余凯旋带着一封毛笔字写的信去找张有金,也就是张成功的父亲。
余凯旋来到一个山村,遇到村妇彩霞(暂且不讨论彩霞这个角色是想象的还是真的)。
从彩霞的回忆中我们得知:
她和张成功都不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,来的时候一个人五岁,一个人八岁。长大以后,张成功想去当兵,但是资格不够!(这个信息很重要,为什么资格不够?)还是彩霞的爸爸认识武装部的人,托关系才去的。
结果张成功自己当兵离开了山村,彩霞却一直留下来成了村妇。
而后,彩霞把余凯旋领到悬崖上找张有金。在这余凯旋知道这封信不是写给父亲的,而是写给自己的,也就是张成功年轻的人格。余凯旋从信里得知,张成功的父亲曾经从这跳崖自杀,原因是其他人把他的几万首诗烧了。
张成功在警察局说自己57岁,如果按2019年张成功57岁算,他8岁随父亲来到山村,50年前就是1969年左右。
1969年是什么年份?为什么张成功和彩霞要跟着父母来村里?为什么张成功不够资格当兵?为什么诗这种东西那时会被烧掉?
答案很明显: 当时中国正在发生两件大事,知青上山下乡和“文革”。
接下来,张成功要求余凯旋做第二件事,去帮开盲人按摩店的老战友。
在这段剧情中,从张成功一笔带过的台词中也透露出非常重要的信息。
张成功从山村如愿以偿当兵后,和炊事班的范志刚成了好朋友,俩人相约退伍以后一起开个小饭馆。但后来两人随着时代的前进分道扬镳。
脑袋里有地雷碎片的老范找张成功借钱手术,但张成功却没有念老战友的旧情,导致老范失明。而张成功当时并不是没钱,买一个大哥大还花了1万多。
在这段故事里有两个关键信息: 开饭馆和大哥大。
“文革”后,对全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最大历史背景,当然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了。一时间,个体户、下海经商、去海南开发房地产等等,都是当时的风潮。
改革开放后,中国第一张编号001的个体餐饮工商执照,发给了在北京翠花胡同开饭馆的刘桂仙。这家饭馆现在还在营业,因为是第一家而且隐于胡同深处,成为北京必打卡的一处秘境。
所以,当年的老范和张成功,有着和刘桂仙一样的小梦想、小目标。但随着两人各走个路,张成功能买得起大哥大,说明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属于混得不错的,而老范混得却比较惨。
由于当时一切“向钱看”的社会大潮,亲情、友情、爱情淡漠,钱成为所有人心中一等重要的事情。
战友情也被很会赚钱的张成功抛在身后,与其借钱给一个伤残,不如自己买个大哥大联系业务来的实际。
就像贾樟柯给他的惊世之作《小武》最早起的超长名字《靳小勇的哥们 胡梅梅的靠山 梁长有的儿子:小武》,分别从友情、爱情、亲情,表现了改革开放对一个内陆小县城的浸透和造成的剧变。这一剧变的核心,就是“利益”当头。
张成功,变成了那种凡事“向钱看”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