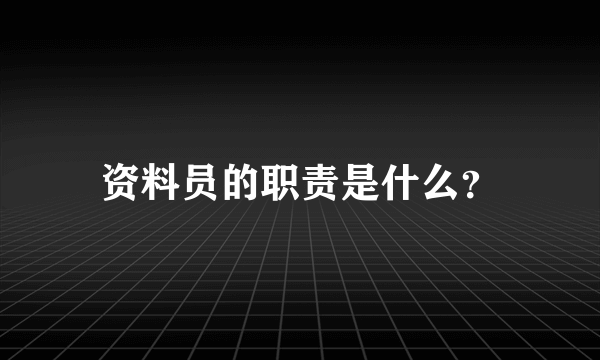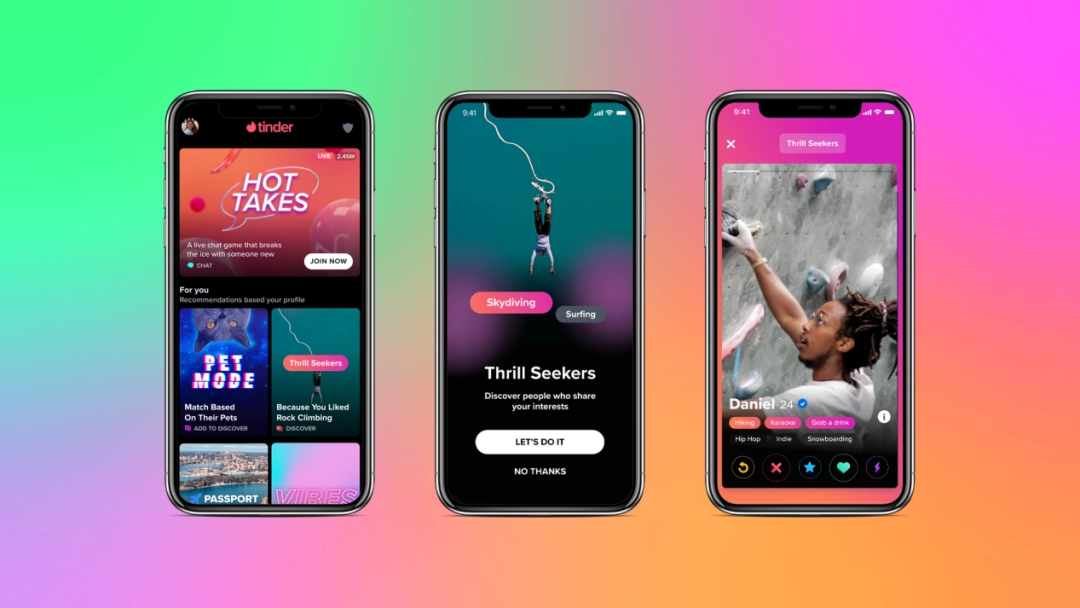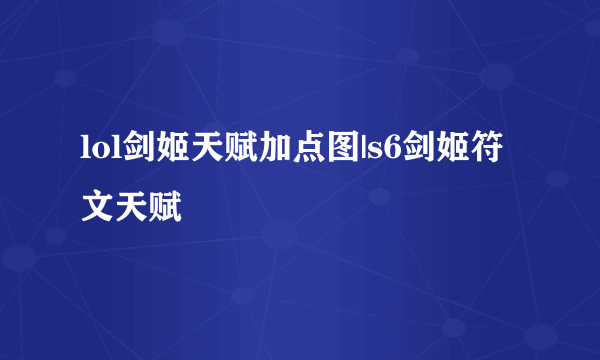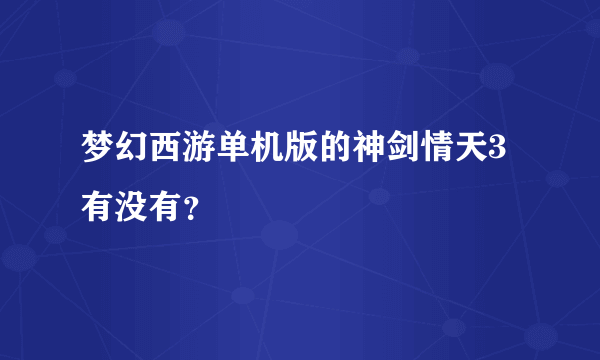斯科特,60年代他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,70年代他曾是欧洲商业电视片领域最富创造力的人。涉足影坛的里德利·斯科特很快成了70年代最有希望的导演之一,1977年的《The Duellists》是一部真实再现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题材影片,该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大奖。1979年的《异形》,再次大获成功,成为一部里程牌式的作品,奠定了他重量级导演的地位,也为他迎得了科幻、恐 怖片大师的美名。1982年他拍摄《2020》(Blade Runner)陷入了麻烦的泥潭,为了影片过于复杂的内容他多次与摄制组发生冲突,最终影片还是遭到了电影艺术家们的抨击,票房也遭惨败,直到90年代早期,这部影片在家庭市场中发行,才重新被公认为是一部科幻电影的杰作。
此后斯科特继续他的事业,1986年拍摄了由汤姆.克鲁斯主演的《诡秘怪谈》(Legend)。1989完成了《黑雨》(Black Rain),迈克尔·道格拉斯在片中扮演一名在日本执行任务的堕落警官。1991年,他的《末路狂花》(Thelma & Louise)获得评论界的赞誉,同时赢得了票房上的成功,影片由吉纳·戴维和苏珊·萨兰登主演,获得最佳导演奖在内的六项奥斯卡提名,影片的成功,又一次证明了斯科特的价值。不过好景不长,1992年的影片《1492:天堂的征服》(1492:Conquest of Paradise)又一次让他走入了低谷,之后的几年中,他一度息影。
1996年,斯科特重整旗鼓,执导了动作片《巨浪》(White Squall),讲述了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在海上的历险故事,影片表现不佳。1997年,斯科特执导影片《G.I. Jane》仍不走运,不得已斯科特暂时当了制片人与他的兄弟汤姆·斯科特(曾于1986年执导《壮志凌云》,1998年执导《国家的敌人》)合作,在1998年他们制作完成黑色喜剧片《Clay Pigeons》后,斯科特再一次回到了导演的位置。2000年他拍摄了《角斗士》(Gladiator),影片由拉塞尔·克罗主演,是一部预算成本达1亿元,长达154分钟的巨作。影片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,评论家大多给予了好评,认为它重现了大制作的辉煌,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它渲染过了头。
1910年斯科特南极探险队挑战世界首批抵达南极的纪录,却在最后阶段深陷于坏天气及成员精神崩溃的恶梦中。在面对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一行已于一个月前率先抵达的事实,失落之余,斯科特一行在回程途中全体罹难。如果以为在南极探险只有苦难,没有欢乐,那就大错了。事实上,探险者们会品尝到许多不寻常的快乐,并且不只是与苦难作斗争的意义上的快乐,更多的是完全正面性质的轻松的快乐。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景物。彻里常常情不自禁地描绘他所看见的美景:在阳光普照的日子,由于光影作用和大海、天空、云彩、积雪、冰峰之间的互相映射,万物都染上了奇妙的色彩。他说得对:南极绝非一片纯白,到处呈现的是亮蓝、翠绿和紫红。到过南极的人也一定会熟悉他的这一感受:面对眼前的奇丽景色,人们很难回想起也许昨天还支配着自己的沮丧心情了。他对企鹅的生活习性观察得特别细致,在书中有极为有趣的描述,很值得一读。在南极生活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快乐,便是摆脱了对现代社会中所谓必需品的需要,不为物所累,真正做到无忧无虑。由于这个原因,彻里把在哈特岬度过的日子视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。最感人的是这些遇难者在临终时日的表现。斯科特大约是最后一个死去的,他的日记坚持写到1913年3月29日。3月17日,在奥茨走进暴风雪之后,他写道:“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以相似的大无畏精神去迎接末日的到来,并且我们确信,终了之日已经不远了。”写完最后一日的日记,他加上一条补充:“看在上帝的面上,照顾好我们的家人。”他还分别给两位难友的夫人写了热情的慰问信,给英国公众写了沉痛的告别信。在后一封信中,他表示:“我并不后悔进行这次远征,它展示出英国人能够承受苦难,互相帮助,即便在面临死亡时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坚忍和刚毅。”搜寻组看到的情景是:帐篷内十分整洁,三具尸体的表情和姿势都显得平静,各人的日记本以及气象日志、地质标本、摄影底片等物件安放得井井有条。一切迹象表明,他们是安详从容地离去的。他想明白了一点: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竞赛,而是对南极进行科学研究,以填补空白。这的确是事实,他们这个探险队有一半成员是科学家,沿途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。更重要的理由是,驱使人们去南极的真正动力是精神上的需要,包括对新知识的渴望,也包括战胜自身弱点的愿望。世上并无天生的勇士,恐惧之心人皆有之,而正是在各种形式的探险活动中,人们以向恐惧挑战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敢。
摘要
搞不清
斯科特目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