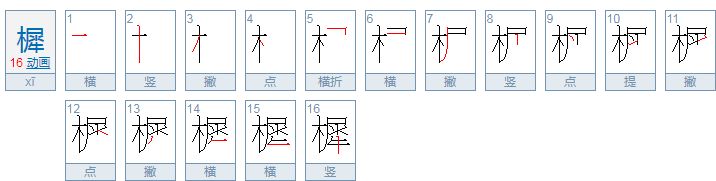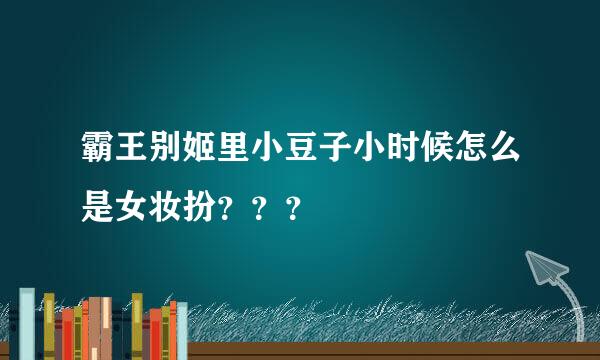
霸王别姬文里写道小豆子妈妈因为是妓女。
自己很贫困却把小豆子打扮的很光鲜。因为是男孩儿,堂子不能养塌肆派着。
所以只能把它交给戏班。也不至于饿死。
还有就是那不是女妆扮,书里写的是,只有戏班的儿男孩必须要把头发剪了。
所以他9岁进梨园的时候头发长一点很正常。
霸王团贺别姬电影影评:小豆子——程蝶衣
初出场的蝶衣的幼时,我感觉到诧异,这个孩子和蝶衣的相貌神情如出一辙,可以预想他长成时那艳丽的倾国倾城。冬天刺骨的寒冷中,他与畸形的手指决绝,与狠下心的母亲决绝。按掌为证的堂上,母亲遗留深绿的锦袍,重重地压在他颤抖的身上,未来的命运重重的压在他身上,那预示他将来荣耀加身的袍子,在孩子恶意的嘲讽中,化为轻烟。
那天,他铭记的是寒冬是抛弃是痛楚,同样还有,一个张狂的男孩,一个未来霸王的关怀。大眼睛眨着,抱着小霸王的被子,火光照在他身上,颤动,他的明眸,颤动。
从此,他成为小豆子。从此,他得到一个小石头。从此,他在戏的乐调中深陷,大爱大恨的绝裂,他将疼彻心扉。
小豆子被石头狠压双腿,疼痛撕裂着,爆炸着,他放肆大哭。“别嚷嚷!!我不爱听!”没
有所谓人道法律,稚鸟无笼就得在森林里披荆斩棘,“人生在世就得有一技之长。”这是现实的血训。
小石头踢开了一块砖头,小豆子愕然的看着那砖块。然后
小石头屁股一下下吃着板子,在雪花中扛着结冰的水盆,风雪割破石头孩的小脸,大笑着说自己练了火丹功,全身正烫着。
小豆子在暖黄的火光中看着石头,轻轻推开那霸王大气的粗莽,把被子围上他,细致地脱掉石头的湿衣,双唇紧闭,被窝中,用细小的臂膀温暖着那粗粗的正气的背,那是他以为可以依靠一辈子的霸王的怀抱。
可惜不是。
小豆子长大了,不同于其他鲁莽的男孩,他把手套在毛套子里喊嗓,他的脸细长尖润,干净苍白,眉毛弯而挑,眼睛黑亮似带湿润,下眼睑浅浅细纹调和着淡青色调,唇形饱满鲜红,身段瘦小,仿佛在群兽中优雅的大鹤,彩绳包裹的碧玉,挺拔秀气。
那几乎永不妥协的《思凡》词句,寄托着小豆子对男儿身的坚持,他在井旁轻舞长袖,脸上扑满华丽胭脂,婉约流彩在他身上舞动,经理的考验来到,他低目浅笑,婉婉道出不知已记多少遍的戏文。
“我本是男儿身,又不是女娇娥。”
他道出此句,才恍若醒梦,惊恐爬上他的嘴角。
小石头暴怒了,一把扯过豆子的大红衣衫,他愤怒地拖着他,那幼弱的虞姬,把他掷在中央的镂花木椅上,滚烫的烟斗随着威胁猛地捅进他的嘴巴,烟臭和高温施虐他的口腔。大人们,瞪着眼睛围观,惊讶得一言不发,暴行渲染着剧痛。石头的发泄完后,扭头去练他的戏,石头的怒缘于他的现实,他的扭头不顾,是段小楼背叛的始曲。
幽怨地看着他,那端坐在皇座上的后,一丝殷红顺着薄唇留下,两行清泪濡湿他的妆容。那是你做的孽。好吧,自此之后。但允了那嘴上的妥协,又是否可得你一生的体贴?
他不嗜睹。但他赌上了。
一个醒鼓,孩子们都回头注视着挽袖而起的王后,他嗫声唱咏,梨涡浅笑,脚步款款向前,戏文娓娓道来,男孩儿们绽开笑颜簇拥着他,因为豆子终于作对了事。那种酸苦的,谁看到?
那天他得到教训,他入戏,他蜕变,他屈服,哑忍着,一切一切,包括在张公公的色欲注目下发抖地小便,被凌辱,欲雹或哭无泪。他还在深宫的回廊中轻添师哥的眉脚,那么被他温柔呵护的男子,在他遭受耻辱后出来时着急地为他披上袍子。但霸王,他明白他吗?
他仲使焦急的发问他怎么了,他可能体会到他的艳妆为何黯淡混乱,他的衣衫为何不整,他为何缄口不语吗?他很冷,他在冬夜被遗弃了,被纷飞的雪花装点的现实击倒,他只得到被美色所诱的征服,毫无暖意。
(那个背着小豆子跑去公公去的爷子,当时我看着,心里惊悚非常。不知道为何有此感觉,那爷子像一种无法抗拒的漩涡,命运把人都卷入深渊,谁都无法挽回,没有比这个更加令人心冷的了。)
也在冬夜,他执意地收留了一个遗孤,看着孤儿在灯下啼哭,男孩圆圆的脑袋在上面排成了圆圈,小豆子,灰色长衫,灰心的冰冷的,他双唇紧闭,眼神空洞。
他是如此美丽。
这是禀赋还是报应?
从此,程蝶衣。
窗外反日呼声四起,烟火呼啸,满地狼藉。屋内,蝶衣,他只细致地顺了顺师哥的马褂,手在衣料上实实一按,笑意洋溢,喜上眉梢。园外管冷冽飞雪还是花好月圆,又何干。
自是一个暗易性别的男子,他会双膝轻碰,柔软,细添举手投足的角度,拨好衣服的下摆,安然一坐,泯然一笑,一手指尖捏扇一手微按衣袖,他在生活中演他的旦角,恍如娇羞的白花。
只顾与他的凝视。戏台红黄蓝绿彩云间,台下道不出含情,也不碍彼此脉脉。
可虽他侠义赤肠,也要那花酒杯中绕指柔,他不作武大打西门,也娶得他眼中嫉恨的潘金莲,却道一凡俗莽夫,弃下你的尖酸讽刺与大声挽留,也怨不得。顺了那个拿翎子的爷,在挑逗中心思看透,又与他人把酒嬉闹,被冰冷的唇舌吻上,那哭花的妆容是王舍宝剑的冷漠,那绝交的话是咬着牙齿挤出来,也寂寞。
扮了贵妃,演了丽娘,不顾看戏的江山已经转换几个朝代,他依旧下鱼卖醉,他依旧展扇道姹紫嫣红,没有霸王也娇娆,可那为他,灰色长衫唱着游园,那个身段,我不知道翻来覆去看了多少次。一如他踱着女王布去取围巾,傲傲的躲开菊仙的披斗篷,也是绮丽,那个步子那个动作,一次次复看,听着牡丹亭的原声,仿佛与戏中的他在耳朵上亲近着,穿越生死,蝶衣。
与四爷碰杯,他舌头轻舔下唇,迷蒙地,舞动银杯,小指轻轻勾起,看在锅上血淋淋的霸王别姬,也像他,杜鹃嘶啼哑血,用玉石俱焚,只为那已许给你的心。
奈何与人调笑乐甚,也只爱那台上欢欣,咋就如斯难得,就要命该被糟蹋?
带出的乖巧郎去着着中山装蹦跳着,忘记了把他捡回来的人在熬着戒大烟的罪,掀翻了水盘,嚣张的眉角已经清除小时恩人落在自己头上的温暖手掌。四儿。你知道么。你娇媚的一句“大王。”伤透了他的心,纵使嘴角再绝强,又奈何解下斗篷后那彻底的冷意?
虞姬不分入戏与现实,道与你听,可那种执拗要嵌进血肉的痴性,谅你那么千万年,也不懂。
嚓地出现的柴火,干脆的冷厉地,在一排排戏服下翻腾,他轻挑秀眉,一脸漠然,微翘的嘴角,讥讽。随它死去,一了百了。
就像他看着苍老肮脏的小楼和菊仙在床上厮混,扭头入雷雨,浇却心头恨。看着霸王撕碎他相依为命的痴绝与尊严,就将那股委屈郁结刺心,揉碎了嘶哑地叫喊出来,责骂的,却还是断壁颓垣,手指着的,是那懂得你的情敌。
你哟,你这女子哟,你那时,终究是个女子。像那人说的,女子说得多么强悍,又哪能道是真正的强悍呢?你争得白了头,碎了心,时光挖走年华,上面多少糜烂,多少变迁,又何道是你一疯魔戏痴,可以承受得起呢?
最后他什么都做不到,因为他是旦角,他是虞姬,他是吧昆腔拿捏得出神入化将展扇收扇的节奏稔熟于心的戏子,一个瘦弱娇柔的“女子”。他声嘶力竭呼喊出来的时候,是肝肠寸断的时候,是了绝尘世的时候,是青衣化灰的时候。
我看戏从是偏心的,我只看着蝶衣,看他戏中如鱼得水,看他撕心裂肺,看他挑高了眉坚硬了唇,婉转出一曲充满妒忌与
张国荣的圆润言语,在剧中好得让我心颤,虽是配音,也觉得,如果是一口粤语尾音的蝶衣,就不配,那男音的清润甜冽,如此合衬,肝肠寸断,欲仙欲死。
只是,其实一直不觉得张国荣美,当初我只觉得他有种凡俗的气质,没有皮特的阳刚,也没有朝伟的灵气。他只是个享受许多赞誉的圈中人。而现在,我只觉得我之前所见的他,生不逢时。他下垂的肩膀撑不起宽大的男装,他留的现代的发型衬不起他的秀美,甚至他身边的娱乐圈,风花雪月纸醉金迷,都不是他这个人最好的注脚。
是他的幸福吗,因为他成为了程蝶衣,他把生命的汁液都挤入戏这个窒息狭窄的蛹壳,可他那么怡然自得。是那也他的不幸吗,他疼痛,他自尽,与高楼伴清风灯影坠下。一如程蝶衣。
直到我得见他的霸王与他的虞姬,我才真正感受到,张国荣,一个超越世俗烦碌脚步的男子,着上干净的青衫,围上洁白的长巾,一件阔大的红锦披风恰到好处地裹实了他的高傲恬静的心灵,舞台上莺莺转转提腔转调,一如那他慢步走过的村间小路,只有这一切,才是真正的张国荣拥有的神韵的归处。
有些人,天生必被某些命中注定冥冥牵引,直到他了解自己的真心。他演了蝶衣,复出后妖艳,或是随了唐先生,为他高歌月亮代表我的心,无论看戏开唱旅行游玩,都有他伴,何求?那头长发,那双红鞋,那小报上浅浅的牵手,那歌唱时隐晦的OK手势,是种默许么,默许一个他,在世人面前,扮上另一个他的戏份。
奈何如何娇纵,也纳不下他的忧郁,也留不住他在戏里。虞姬出戏而为死,霸王眼中的自刎,何尝没有文华脚边的血艳?
对。我迷恋他。都不知道因为他的蝶衣,我释放出多少压抑的屈痛,也因为蝶衣,再尝品赏美人的悸动。我不道平实言词,我固执觉得,他们的情戏若如宝黛,又何堪浅俗言欢?
“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爱绵绵无绝期”
小楼不道与蝶衣的,他道与了你,却了人世,谢了欢言,那些离开,也一缕烟丝飘舞,背后,曾经的火树银花,也惹得喧嚣欢腾,只说,我们曾经有过,见到那惊鸿一瞥美艳如斯,此恨经年了,也随得人尽去,无怨无悔。
参考资料
豆瓣:https://movie.douban.com/review/2103594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