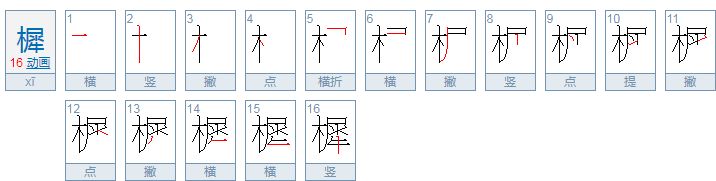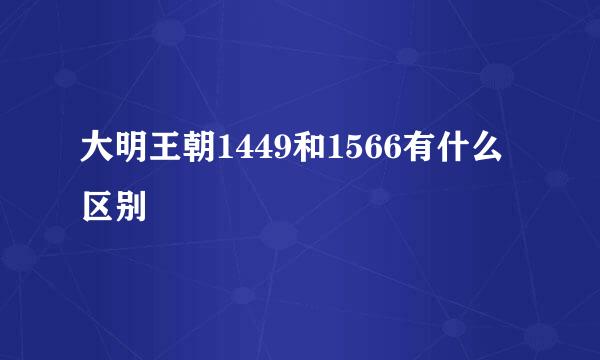沈从文(1902-1988)原名沈岳焕,苗族湖南凤凰县人,14岁时,他投身行伍,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,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,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,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,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,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,1988年病逝于北京。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《石子船》、《从文子集》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《边城》,《长河》等6部中长篇小说,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,他认为“美在生命”虽身处于虚伪、自私和冷漠的都市,却醉心于人性之美,他说:“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,那可不是我,我只想造希腊小庙。选小地作基础,用坚硬石头堆砌它。精致,结实、对称,形体虽小而不纤巧,是我理想的建筑,这庙供奉的是“人性”(《习作选集代序》)。 沈从文春饥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,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,融写实、纪梦、象征于一体,语言格调古朴,句式简峭、主干凸出,单纯而又厚实,朴纳而又传神,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,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。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,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,给人教益和启示。中篇小说《边城》是他的代表作,寄寓着沈从文“美”与“爱”的美学理想,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,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,反映出湘西在“自然”、“人事”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,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,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。 从作品到理论,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,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,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,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“和谐共存”的,本于自然,回归自然的哲学。“湘西”所能代表的健康、完善的人性,一种“优美、健康、自然,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”,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。 沈从文的一生是烂森洞坎坷的一生,是奉献的一生。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《边城》、《湘西》、《从文自传》等,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。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,并被美国、日本、韩国、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,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。 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,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。三四十年代,他是北方文坛领袖,40年代末,主要因郭沫若“桃红色作家”的指斥,沈从文退出文坛,长期被尘封土埋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沈从文的声誉鹊起,“大师”的赞誉不绝于耳。人们对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可能略知大概,详情却未必了解。一、退出文坛 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郭沫若《斥反动文艺》一文,刊发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《抗战文艺丛刊》第一期上。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“桃红色作家”,“存心不良,意在蛊惑读者,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”,还说沈从文是“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”。同期《抗战文艺丛刊》还刊登了冯乃超的《略评沈从文的〈熊公馆〉》一文。沈从文的《熊公馆》发饥枯表在《国闻周报》上,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。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“人格的素朴与单纯,悲悯与博大,远见和深思”,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,体现了“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”。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,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。1949年初,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“打倒新月派、现代评论派,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”的标语。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,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,沈从文自杀未遂,从此退出了文坛。 事实上,郭沫若冯乃超讨伐沈从文,只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之作,此前此后,对沈从文的类似批评屡见于报章。论者多用阶级斗争理论、典型化理论理解他的作品,如韩侍珩《故事的复制——评沈从文著〈月下小景〉》(1934),贺玉波的《沈从文的作品批判》(1936),凡容《沈从文的(贵生)》(1937)等,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,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,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。在三四十年代,沈从文还因“京派与海派之争”,“禁书政策之争”,“‘差不多’问题之争”等文艺论战,被左翼批评家批评过;西南联大时期,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,也受到他们的种种非议。新中国成立后,新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。在王瑶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(1954),丁易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略》(1955),刘绶松的《中国新文学史初稿》(1956)这3部学科奠基之作中,沈从文以反面形象“叨陪”其中。论者发展了左翼批评家的主流观点,并将其系统化。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严峻,沈从文作为一个“落后的”,甚至是“反动的”现代作家,终于从“纯洁的”的文学史上消失了。二、再受关注 沈从文一生著述浩繁,刚刚出版的《沈从文全集》32卷,1000多万字。20世纪中国产生这样一位作家,是一个奇迹,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谩骂抹黑以及漠视能够抹杀的。 对沈从文文学地位的正面评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,与左翼批评同时出现。鲁迅早期虽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,在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时,没有收沈从文的作品。可是据斯诺回忆,鲁迅在与他谈话,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时,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,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沈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。另二位文坛巨匠周作人、老舍在1934年回答期刊提问,他们最喜爱的书是什么时,都提到沈从文的《从文自传》。这些关于沈从文正面的议论和态度,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,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此外,苏雪林在《沈从文论》(1934)一文中,更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,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,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。刘西渭在《〈边城〉与〈八骏图〉》(1935)中力图提炼沈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征,他对《边城》和《八骏图》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,给人清新的感觉。但总体来说,1949年之前的正面评价是零散的,感性的。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,拨乱反正伊始,沈从文在经历了长期尘封土埋之后,重新受到重视。这个时期对沈从文的评价明显带有论争性:被激情鼓动着的新锐研究者,要求对沈从文重新评价;保守者从维护传统出发,拒绝接纳沈从文这样的“异端”。两种倾向的冲突酿成多起事件,如1980年,丁玲写《也频与革命》,1983年,朱光潜的《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》,都引发了讨论。争论的结果,对沈从文的认识逐渐回到常识和理性的层面。随着沈从文声望鹊起,素称谨严,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著述,如唐主编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》(1984)也把沈从文吸纳进来,在“五四文学传统”中给了他一席之地。自此,沈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。 在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,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,在王润华、司马长风、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,一直薪火不灭。80年代,又一批海外学者如聂华苓、金介甫等,对沈从文进行了更深入、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。随着他们的著述在内地传播,他们对沈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、历史的考证和研究,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,给内地学者以极大启发。此外,日本的沈从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搜集、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卓有成效。80年代中期以降,国内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,取得了突出成绩。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,与湘西区域文化的复杂联系;沈从文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,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,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;沈从文思想、人物、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;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、自足性和目的性,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研究,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,沈从文后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,创作心理研究等等。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,为90年代后期沈从文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。三、新的座次 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,又赶上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,二者合力,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:作家排座次。 在文学史的序列中,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,金介甫是第一个。他在《沈从文传》(时事出版社1991年7月中文版)引言中写道:“在西方,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。他们都认为,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,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,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。”金介甫反映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方汉学家的普遍意见。在这段文字中,“少有的几位”、“伟大”的说法,以及和鲁迅并列,都是极高的赞誉。 1994年,王一川主编的《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》(分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4卷)由海南出版社出版,此文库以“文学大师”标目,其小说卷将鲁迅、沈从文、巴金、金庸、老舍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,却把茅盾等排除在外,由此引起强烈反响。在文库的小说家排名中,沈从文列第二位。编者给沈从文获得如此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:“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”;此外,近年对沈从文频繁使用的“大师”称号肇始于此。 1995年,钱理群、吴晓东推出了排在最前列的7位现代作家的名单。他们在《“分离”与“回归”——绘图本〈中国文学史〉(20世纪)的写作构想》(载《文艺理论研究》1995年1期)一文中写道:“在鲁迅之下,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,即老舍、沈从文、曹禺、张爱玲、冯至、穆旦。”沈从文在全体现代作家中排名第三。 1999年6月,《亚洲周刊》推出“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”,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,遴选前100部作品。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、作家,如余秋雨、王蒙、王晓明、谢冕、王德威等。在这一排行榜中,鲁迅以小说集《呐喊》位列第一,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名列第二。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,《边城》则属第一。 这些产生于20世纪末的排名,有的针对作家沈从文,有的针对小说家沈从文,有的针对沈从文的个别小说,虽然范围大小不一,却都在二三名之间。在世纪的转折时期,一些作家或被读者遗忘,或被史家遗弃,而沈从文却跻身于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,目睹这种变化,不禁令人感慨唏嘘。 早在30年代中期,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:“……说句公道话,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。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。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,播得远。我没有方法拒绝。”(《从文家书·湘行书简》)果然,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,成为经典,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