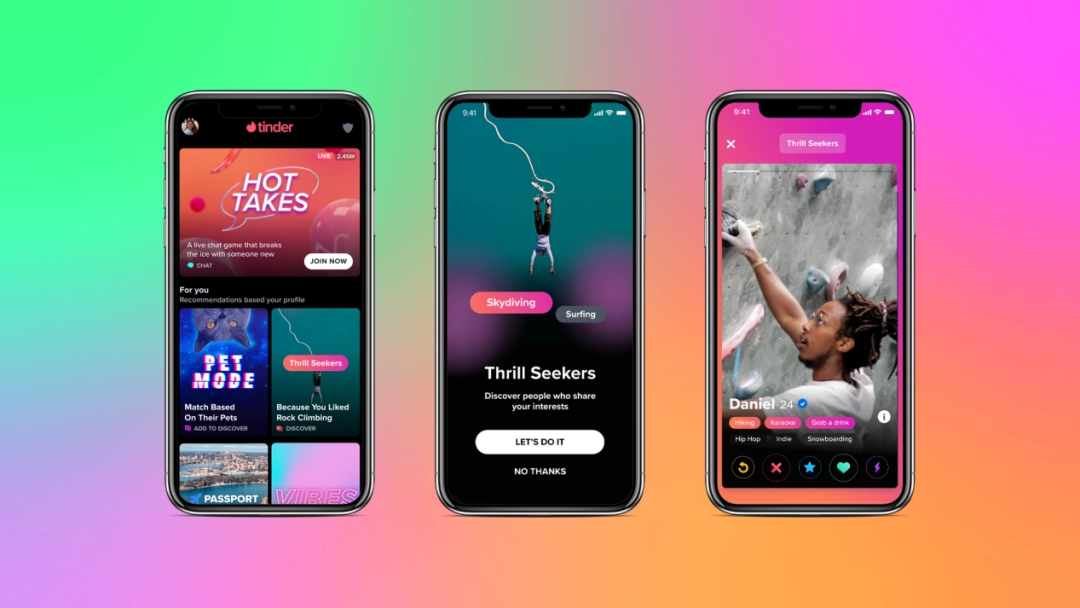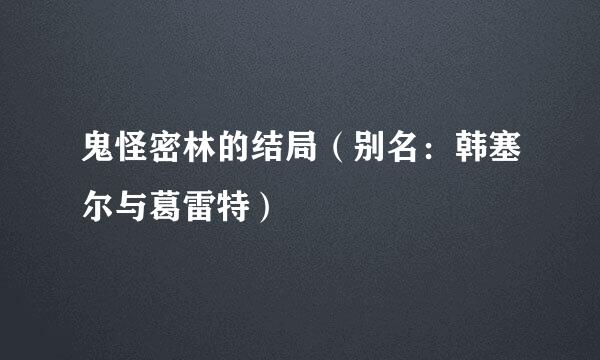梁衡:山西霍州人。1946年出生,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。历任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、《光明日报》记者、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。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、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。 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、散文家、科普作家和政论家。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。 他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;新闻三部曲《没有新闻的角落》、《新闻绿叶的脉络》、《新闻原理的思考》;在散文创作方面,过去二十年他主攻山水散文,深得古典山水文章的传统,行文草本有灵,水石有韵。近年来又致力于人物散文,特别是历史伟人名人的写作,《觅渡,觅渡,渡何处?》、《红毛线、蓝毛线》等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。 有散文集《夏感与秋思》、《只求新去处》、《名山大川感思录》、《人杰鬼雄》、《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——梁衡卷》等。 作品曾获青年文学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;1996年在《佛山文艺》发表的散文《忽又重听“走西口”》获《美文》、《文学自由谈》、《佛山文艺》三家联合举办的“心系中华”散文征文优秀奖。有散文三篇《晋词》、《觅渡,觅渡,渡何处》和《夏感》入选中学教材,近年《海思》也被选如鄂教版语文中学教材。 评赏梁衡的散文《夏感》 在诗人作家笔下,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。也许,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,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;也许,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,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渲泄吧;所以,吟春咏秋,古今舞文弄墨者,几乎趋若过江之鲫。而夏呢?也许它太热太酽太稠密太有点“浓得化不开”了,因此,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。如是,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“快乐原则”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?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阙如!即使有人写写,也难免写成“毒恶的灰沙阵”,“烫着行人的脸”,“干燥炎热的风”,“凶恶的嘶叫着”,“人象快干死的鱼”,“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(引自茅盾、老舍、高尔基、罗曼罗兰诸人的作品)——一种作为艺术的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;或者,写成“日常睡起无情思”余基(杨万里),“手倦抛书午梦长”(蔡确)——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。 可是,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,从人所寡言处言之,“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这间的黄金的夏季。”须知,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。而他在这篇作品中所创造的清隽境界、丰厚含茹和高致的美,他的英华吐纳的娟秀语言,更令人由衷叹服。《夏感》确实够得上是当代散文中一篇难得的精品。 二 《夏感》一开始,作者这样写道:“充满整个夏天的是一个紧张、热烈、急促的旋律。好象炉子上的一锅冷水在逐渐泛泡、冒气而终于沸腾了一样,山坡上的芊芊细草渐渐滋成一片密密的厚发,林带上的淡淡绿烟也凝成一堵黛色长墙。”在这里,朴实得有点稚拙的“一锅冷水”的比喻,新鲜的活脱脱的“密密厚发”的拟人,巧妙精当的“黛色长墙”的词汇选择,作者仿佛在进行俯视式竖迅谨扫描一般,寥寥几个镜头,就勾勒出夏景的宏观。而“烦人的蝉儿,潜在树叶间一声声地长鸣”一句,则宛然上述一组镜昌渗头的画外音乐。这儿的“烦”,显示着夏的热力,却绝没有沉闷的心迹;传达着夏的喧闹,毫无燥乱的踪影。悠悠溢出树间的声声长鸣,映衬着夏景的明快色泽,烘托着一种“蝉噪林逾静”的氛围,也更加表现出夏日大地的充实、厚重和沉稳。于是,在声色互补、虚实交融之中,作者已经为全文定下了昂扬积极的主调。 接着,作者摆平视角,镜头下移,好象在纵目远眺这广袤的原野似的,望着翻滚的麦浪“扑打着远处的山,天上的云,扑打着公路上的汽车,象海浪在涌着一艘艘的舰船。”这里,作者呈现给我们的,已不是现实世界的简单还原,而是一种意化了的风物,是外在客体在作者心灵屏幕上的闪烁;或者说,是折射着作者情感光束的时代投影。然后,一阵浮动着的热风,“飘过田野”,似乎是给远眺的作者、也似乎是给读者吹送来“已熟透了的麦香”。这一笔点染,不仅恰到好处也恰如锦上添花。正如前面蝉鸣的烘托体现为一种声与色的交融一样,这儿的点染则体现为一种色与香的谐和。如果说,前面的烘托是一种氛围的点化,那么这儿的点染则是一种情致的昭示——昭示生活的丰腴和饱满。作者就是在如此详尽地进行了铺垫之后,从容不迫地把他的笔触导向文章意蕴的致力点——“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,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,在田野上滚动,在天地间升腾”。 这才是作者自己的夏感,这才是作者自己所发现、所体认、所慧识的独到的夏感。从这里,作者又仿佛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一段精妙的议论:“春之色为冷的绿,如碧波,为嫩竹,贮满希望之情;秋之色为热的赤,如夕阳,如红叶,标志着事物的终极。夏正当春华秋实之间,自然应了这中性的黄色。”这一段议论,构句独树一帜,用语别开生面,排比对偶驾轻就熟,在古色古香中显现着一种难得的理趣,即一种优美的情趣与深沉的意理相结合而滋生的抒情美感。这一段议论,对前面之意蕴致力点,是发生,是拓进,是引深;实际上,也是作者对自己所发现、体认、慧识的夏的质性的一种哲人式抽象与鞭辟入里的诠释。那么,这种质性意味着什么?作者很快就一语道破了。原来,“那春天的灵透之气”所积蓄所酿成“磅礴之势”,正是一种“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”的伟力的奔突,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“承前启后,生命交替”的律动,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。作者热情讴歌的,就是这样一首力、生命与创造的诗。 三 梁衡同志赞美的夏,是麦浪翻滚、麦香吹送的夏,是“金色主宰了世界上一切”的夏。这是何方之夏?显然,作者的注目点是非常明确的。在那段精妙的议论后,他这样写道:“你看,麦子刚刚割过,田间那挑着七八片绿叶的棉苗,那朝天举着喇叭筒的高梁、玉米,那地上匍匐前进的瓜秧,无不迸发出旺盛的活力。这时,他们已不是在春风微雨中细滋漫长,而是在暑气的蒸腾下,蓬蓬勃发,向秋的终点作着最后的冲刺。”这里,作者的视角好象在渐渐拉近,镜头也从宏大转入精微。于是,一个一个机趣盎然的大特写跃入了我们的眼帘。一个“挑”字,让我们几乎感到了棉苗均匀有力的喘息;一个“举”字,让我们差不多感到了高粱玉米摇头晃脑的欢悦;一个“匍匐”中,我们同样感到了瓜秧的腰肢抖动,蜿蜒蛇行。它们仿佛都在紧紧抓住这美好的年华大显身手,不舍昼夜地向着自我的完善和神圣的奉献而奋勇“冲刺”。一句话,出神入化的描绘让我们从这些夏的宠儿身上,感到了人的丰采,人的气度,人的灵秀。福楼拜曾经说过:“不论描写什么事物,唯有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。我们必须不断地苦心思索,非找到这个词不可,而绝不能为了逃避困难,用差不多的词句敷衍了事。”梁衡同志的这一段文字,精雕细刻,丰姿绰约,作者之惨淡用心昭然,同时也是对福楼拜的“一词说”的生动实践。这段文字,不仅构成全文意境的有力依托,而且也成为以金色为基调的夏的主体形象的丰满和强化。 审视作者所描绘的一切,我们恐怕很难想到那稻谷飘香的锦绣江南,也恐怕很难想到那牧草连云的苍茫塞外。我们首先想到的,恐怕应该是那雄浑壮阔的黄河流域了——那八百里秦川,那三晋高原以及那横踞冀鲁豫的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。是的,正是这凝重厚实的黄土地,哺育了我们的民族,润泽了中华数千年的灿烂文明,而作者本人也作为中央报纸的记者并多年驻节于斯。所以,他把黄土地之夏,作为自己纵情礼赞的典型观照物,就不仅有其熟悉生活的意味在,且也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和形而上的寓义在。 四 当然,《夏感》的作者并没有把他的镜头仅仅停留在夏的景观上,而是让自己的视角渐次由表层进入肌里,对准了我们这个星球的真正主宰——人。夏日里生命在交替,夏日里作物向秋的终点最后“冲刺”,这种生机勃勃的运作,固然有大自然永恒代序的机制,但不可不论的是,自从人类参与其间后,它多半已成了作为万物灵长的我们之意志的对象化,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。人,是夏的色彩的真正涂染者;也正是人,拨响了夏的紧张的旋律。“田间那些挥镰的农民,弯着腰,流着汗,只是想着快割,快割;麦子上场了,又想着快打,快打。”“麦子打完了,该松一口气了,又得赶快去给秋苗追肥、浇水。”这一段文字,作者似乎只是漫不经心,信笔写来,与前面一丝不苟的刻镂简直形成了鲜明的差距,表面看甚至给人一种拙讷浅陋之感。其实,白描的语言形式正契合着质朴的内容,如果把一连串形容词堆在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,也许形成的倒是一种美的造作。所以,作者此处的不施铅华,实在也是合情合理之笔。 那么,作品的艺术濡染力如何强化呢?梁衡同志所运用的妙着是——细节。“他们早起晚睡亦够苦了,半夜醒来还要听听窗纸,可是起风了;看看窗外,天空可是遮上了云。”这几个细节,与上述快割快打快追肥浇水之类在叙述特色上一脉相承,构成了该段文字恬淡平实的整体风格。这几个细节,乍一看似乎有点司空见惯,品嚼再三,就象使人感到它独有的韵味。“听听窗纸”,“看看窗外”,在夏的紧张旋律的侧写,是夏的快节奏***,也是作者运用间接表现手法推出的心理镜头。它,外化了“每一根神经都被绷紧”的款款心曲,使我们在想象的空间看到了他们急切的目光、企盼丰收的焦灼以及与夏的律动所共鸣的人的感情律动。在几个细节,极其平易而又极易其传神,明丽天然而又活灵活现,用“看似平常最奇崛”来形容它,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。可以说,如果换一个其他细节取而代之,作品的魅力就会大大削弱。 有趣的是,梁衡同志的《夏感》,全文正好六百六十六字。这在今天,恐怕是难得的短文了。然而,梁衡同志却凭借这为数不多的文字,构筑起如此精美的世界。它,使我们想到玲珑的雅雕、小巧的盆景,想到一方素绢,一块碧玉、一泓清澈的小溪、一簇秀丽的山花。过去评价散文之美,有所谓“人生宝、智慧宝、美丽宝”一说,而“六六”,在我们民族习惯中,向有和顺、如意、吉祥之意谐意。《夏感》正是这样一篇三宝兼具蕴藉着和顺、如意、吉祥美好等含茹的杰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