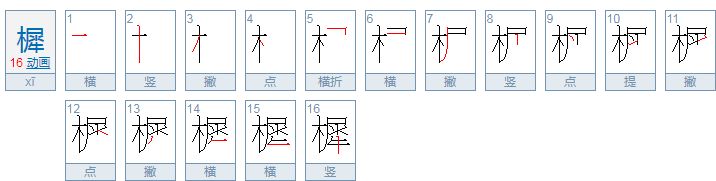明儒学案原文及翻译如下:
翻译:
从过去到现在关于理学方面的专著,前有周汝登的《圣学宗传》,近有孙奇逢的《理学宗传》。二书罗列各家学说很完备,但陶望龄在给焦竑的书信中说:“周汝登自己认为身居山麓江畔,见闻狭窄孤陋,曾经希望广泛搜集书面资料和口头资料,增补所遗漏的部分。
不敢就说这本书已经是定型的著作了。”况且各个理学家自己有自己的宗旨,而周汝登持守发挥禅宗学说,搅和金银铜铁铸成一器,这是周汝登本人的宗旨,不是各个理学家的宗旨啊。孙奇逢混杂收录,不做进一步的审察区分,书中评判注解所涉及的稿答地方。
不一定就抓住了各家学说的要领,而他的所见所闻也如同周汝登一样。研习者观看我这本书,然后会知道周汝登、孙奇逢两家的疏漏简略。大抵某个人的学说具有宗旨,是这个人独树一帜的地方,也是研习者研习这些学说得以入门的地方。
世界上的道理无穷无尽。如果不用一两个基本概念来限定,怎么能统括那些无穷的道理而使它掌握在我手中!所以宣讲个人学说却无宗旨,即使具有独到见解,也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丝呀。研习者不能抓住这些人学说的宗旨,即使阅读他的著作,也像张骞首次来到大夏。
摸不清月氏对西汉的真实意图。我这部《明儒学案》,区分各家学说的宗旨,像拿灯照影一样。杜牧曾说过:弹丸在方盘中滚动,横着滚、斜着滚、转着滚、直着滚,滚到哪里停住了,不能全部猜得到,但肯定可以知道的是,弹丸不能滚到方盘外面去。宗旨大概也像这样罢了。
我曾说过,明朝的文章和业绩,都赶不上前代。唯独在理学方面,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。细枝末节,全都辨别得清清楚楚,的确能阐发出先儒所未曾阐发出的东西。二程、朱熹排斥佛教,虽然说法很多,总是停留在表面上,对佛教中越貌似有理而越淆乱经义的那些理论。
终究还是指不出来。明儒却在最细微的地方,使佛教连逃遁的影子都没有了。陶望龄也指出过:“如果拿见解来说,当代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,在很大范围内有超过先儒的。”这与我的说法不谋而合。常常见到编辑先儒语录的人,只是汇聚摘抄好多条。
却不知道什么叫作取舍的标准和用意。先儒们一身的思想宗旨不曾经透露出来,怎么能够看出他们的学术总值呢?我这部《明儒学案》,全从先儒的全集中抽取要点、探求宗旨,未曾袭用前人的旧有专著。
儒家学者键兆慧做学问,和佛教禅宗五派一定要把本派分别上推到青源、南岳不同。孔夫子已经什么都学,周敦颐不靠传授就使理学肇兴,陆九渊没有师承也自成一家。然而在此过程中,从二程到何基、王柏、金履祥、许谦,经过数百年之后。
还一直奉守本派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所确立的宗旨。这决不是像佛教禅宗那样附会源流才罢休。因而我这部《明儒学案》,依据传授系统,分成各个学派。那些异学突起的人,以及不像异学突起者那样显光的人,统统列入诸儒学案。
做学问的原则是:以各个人独立探讨确有所得为真学问。凡属依傍或因袭他人,照样子画葫芦的,不是随大流的书呆子,就是抄缮经书的行业。我这部《明儒学案》所编列的,既有志向极端化的独立见解,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。
研习者对于他们的不同之处,正应当注意加以理会,所谓本原相同而分支各异呀!用水知水,哪里算得上是学问?胡大时跟随朱熹求猜租学,朱熹让他研读《孟子》。
有一天朱熹问胡大时:《孟子》中“至于心就偏偏没有相同之处吗?”这句话是指何而言?胡大时用“所见”二字解答。朱熹认为不对,并且批评他读书粗心大意,不认真思考。胡大时下来后苦苦思考,因而得了病,朱熹这才告诉他。古人对于求学的人。
不轻易传授点拨达到这种地步,大概是想让他自有所得呀。即便是佛教,也最忌讳道破真意了,一道破真意,人们就像拿光亮照黑影一样做游戏了。我这部《明儒学案》,不免内容庞杂凌乱,研习者读过后只是增加一些见识,不去研究原著,自有所得。
那么我反而因为这部书而对天下后世犯下罪过了。本书搜罗很广泛,但一个人所见所闻很有限,还有待于继续访求。
即便是我曾经看到而又遗失的,如朱布衣的《语录》、韩苑洛、南大吉、穆孔晖、范环诸人的文集,都不曾收采进来,海内肩负学术文化的传播的重任的人,别舍不得指教我。这不是后学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啊!